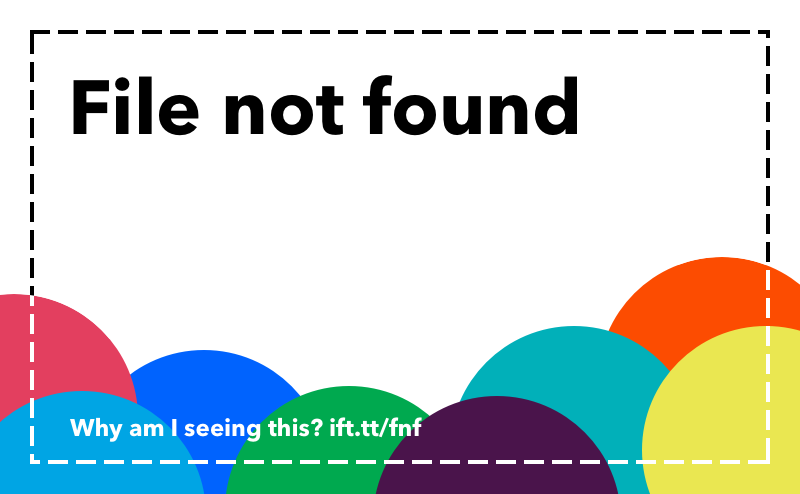
二十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於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二十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一九八九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我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的日记:“星期一(一月十六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一、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二、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三、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一九八九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一九八○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一九八五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牌本来二角八,一下子涨到三角二,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一百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我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的日记:“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日记过於简略,补充如下: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於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於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再就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我发言中还举了江泽民一九八七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真的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五月十八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五月十九日上午八时的日记:“前天(五?一七)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十八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十八号一早,六时五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五十七路公交车。三十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八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於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鎔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中有记录:“一、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二、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三、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採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六四”后我带了三天黑纱我六月五日上午七时十五分的日记:“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这个政府罪该万死!“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我六月六日上午八时的日记:“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四十年来所没有。“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五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当时北京已经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游行,但坚决反对开枪;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丧,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示威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示威!”还有人见到问:“你怎么还没被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我六月二十七日晨七时的日记: “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十七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二十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六四”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我!江泽民“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我八月六日上午九时的日记:“前天,八月四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八时二十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三百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缇、刘异龙、王芝泉……在“六四”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鎔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五月十八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九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鎔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複.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採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江正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作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作为市委书记的江已经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导报》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本立,还抓了张伟国。人是会变的。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别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锺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慑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淒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时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via /r/China_irl https://ift.tt/VFjUw2z
Comments
Post a Comment